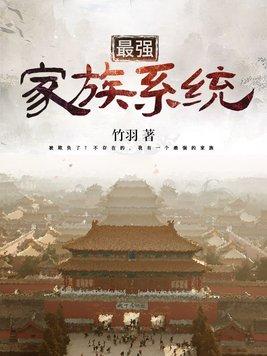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华娱:从神棍到大娱乐家 > 第五百七十九章 球状闪电中为雪糕加更(第8页)
第五百七十九章 球状闪电中为雪糕加更(第8页)
只不过这一次丁仪遇到的是陈光、林云、张彬、郑敏、格莫夫等所有人毕生研究的成果展示,他看着陈博士在电脑上演算的数学模型,和调整了研究方向后基地这大半年来的数据概况……
“嗯……小陈,你知道哪里有卖烟丝吗?”几个小时后的丁仪示意了一下自己的烟斗,语气淡然随意。
只不过说话也不再混不吝了,口水也不往下流了,睿智的思考又占据智商高地了。
“丁教授,您同意了?”陈光喜出望外,甚至第一次见到他的模型的丁仪,已经在刚刚的展示过程中展示出一些真知灼见了。
毫无疑问,他就是这个项目现在最奇缺的基础物理专家。
从因父母被球闪掠杀燃起毕生斗志的陈光,到对超自然、新概念武器无限迷恋的林云,现在加上了一个只对“鲜货”感兴趣的物理学“老嫖客”。
现场所有的业内人士都看得出,这是好莱坞商业片中喜闻乐见的“最后一块短板补齐”。
关于球闪的捕捉和揭秘,要进入一个快车道了。
进入研究基地、获悉了实验全貌的丁仪迅速开始乐不思蜀,他在陈光、林云以及其他所有数学家、武器专家研究的基础上,对现在的困境给出了明确解决方案。
首先,在物理学常识中,带电区域本就是禁飞区,此前两架武直9的意外事故彰显了这一点。
丁仪提出北航有一种氦气飞艇,但它的操纵精确性能不能保证放电瞄准还不清楚,或者能让武直9的绝缘变得和穿着屏蔽服的飞行员一样就好了。
这句话提醒了陈光,也给观众埋上了影片前十几分钟就挖下的坑——
张彬,那个被学生赵雨玩笑为最喜欢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研究的导师,他曾经发明过一种性价比极低的防雷涂料。
只不过当部队接张彬来到基地时,陈光才知道后者已经身患血癌。
这是常年的忧思所致。
一个个问题的解决步伐不停,在丁仪的组织下,终于在他参与研究三个月以后,开始了第一次“球闪捕捉实验”。
两架直升机如约飞起,陈光和老师张彬坐在其中一架,林云坐在另一架。
前两者需要登机根据实况指导飞行员,张彬是自己强烈要求登机观看的,因为他对自己发明的防雷涂料的信心,也是对陈光、丁仪等人研究成果的期待。
两架直升机开始慢慢地相互靠近,一声清脆的爆裂声之后,电弧开始链接,所有人被笼罩在一片刺眼的蓝光之中。
由于两机距离很近,电极又处于机身的下方,所以陈光等人只能看见电弧的一小段,刺目的蓝光让人不敢直视。
戴上护目镜的张彬几乎抑制不住将要跳出胸腔的心脏,和同样心潮澎湃的陈光就这么等着飞机来回扫描了半个小时。
很可惜的是,一无所获。
天上地下的所有人都保持沉默,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反而是身患绝症的张彬。
“小陈,坚持下去,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定你们是对的。”他顿了顿,在影片中第三次重复了自己的嘱托:“如果有什么发现,记得告诉我。”
镜头极其缓慢地推近,最终定格在张彬的面部特写上。
画面构图刻意营造出一种孤寂感,他被病痛折磨得异常消瘦的脸庞占据了大部分画面,背景是模糊的、空旷的夜空和闪烁的仪器,仿佛他独自漂浮在一片由数据和未知构成的虚空之中。
陈光心如死灰,讷讷地看着他的面庞,不可避免地想到如果有那一天的话……
应该已经天人永隔了。
电弧的亮度渐渐减弱,超导电池中的电能也快耗尽,耳机中响起了林云的声音:
“各机注意,熄灭电弧,相互脱离,返回基地。”
她的声音依旧听不出什么情绪,特别是在这种军事实验上,她把所有人、包括自己都当成工具,合规合法使用即可。
就在电弧光芒即将熄灭、夜空即将重归黑暗的瞬间,耳机里突然传来一名飞行员急促而清晰的呼叫:
“发现目标!电弧1号机方向,约三分之一处!”
这声呼喊如同惊雷,在沉闷的机舱内炸响。
陈博士和张彬几乎同时浑身一震,两人不约而同地猛地扑向舷窗,急切地向后方黑暗中望去。
镜头紧紧跟随着他们的视线:起初是模糊的黑暗,随即,一个橘红色的光点闯入视野。
它并非静止,而是沿着一条变幻莫测的、优雅而诡异的曲线缓缓飘行,身后拖着一条淡淡的尾迹。
最令人惊异的是,在高空强劲的气流中,它似乎完全不受影响,仿佛存在于另一个维度的空间,与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则格格不入。
特写镜头迅速切换到陈光和张彬的脸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