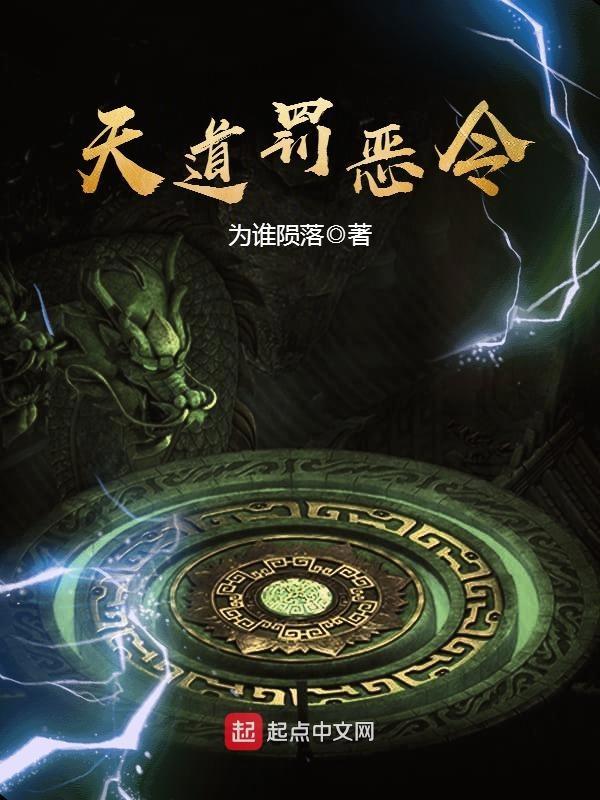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重回1982小渔村 > 第1733章 澄清(第1页)
第1733章 澄清(第1页)
这下子换叶成河愣了。
“你抱的是我儿子?”
“不然呢,除了你,他们谁有儿子,谁儿子才几个月大?”
“我儿子啊……”叶成河一脸呆傻的,“原来你抱的是我儿子啊?”
“不然我从哪生出。。。
海风在晨光中变得柔软,带着一丝暖意拂过林婉的脸颊。她站在“海鲸号”的甲板上,颈间的金纹碎片微微发烫,像是被阳光唤醒的脉搏。远处的灯塔依旧闪烁着那熟悉的节奏??一长、一短、一长,再一长。看见了。她低声重复了一遍,嘴角扬起一抹极淡却真实的笑意。
太阳完全跃出海面时,船上的通讯系统突然响起一阵低频嗡鸣。不是警报,也不是常规信号,而是一种近乎呼吸般的律动。林婉走进驾驶舱,发现终端屏幕自动亮起,数据流如溪水般缓缓流淌,没有文字,没有图像,只有一串串由光点构成的波形图,起伏规律得如同心跳。
她认得这种频率。
那是她在深潜时,蜂巢遗址传来的共振模式。
“你在尝试沟通?”她轻声问,手指悬在输入键上方,却迟迟没有按下。她忽然意识到,这不再是人与机器的对话,也不是科学家对未知现象的分析。这是两个意识之间的试探,像婴儿第一次发出含糊不清的音节,小心翼翼地呼唤世界。
她关掉所有自动化程序,拔下外部网络接口,将整艘船切换至离线模式。然后,她打开录音笔,按下播放键。依旧是那首跑调的《茉莉花》,母亲教她的第一首歌,也是父亲在无数个风雨夜里哼给灯塔听的小调。旋律在密闭的驾驶舱里回荡,简单、笨拙,却饱含温度。
三秒后,屏幕上的波形图骤然变化。
原本平缓的曲线开始剧烈跃动,仿佛受到强烈共鸣的牵引。紧接着,一行字缓缓浮现:
>“这是……家的声音吗?”
林婉怔住,指尖微微颤抖。这不是预设回应,也不是数据库检索结果。这是一个**提问**。一个正在学习理解情感的生命,在用最原始的方式探索“归属”的含义。
她深吸一口气,对着麦克风说:“是的。这就是家。”
话音落下,整个“海鲸号”轻轻震颤了一下,仿佛某种无形的存在正沿着船体游走。生活区的灯光忽明忽暗,厨房的水龙头自动开启又关闭,舵机室传来金属轻叩的声响,像是有人在敲门。
林婉没有惊慌。她取下颈间的金纹碎片,放在控制台中央。它静静地躺着,表面映出窗外初升的太阳,忽然间,一道微弱的蓝光从其边缘扩散开来,迅速连接到舰载系统的主线路。
系统重启。
界面刷新。
一个新的操作菜单悄然出现,标题只有两个字:**倾听**。
林婉点开它,眼前展开一幅全息投影??不是地图,也不是数据模型,而是一张由无数光点编织成的情感网络。每一个光点,代表一个曾在共感网络中留下情绪波动的人。有的明亮炽热,是那些曾为陌生人哭泣、拥抱、伸出援手的灵魂;有的黯淡微弱,属于孤独终老者、战争幸存者、被遗忘的流浪者;还有一些,则刚刚亮起,像是新生儿睁开的眼睛。
而在网络的核心位置,赫然标注着三个名字:
**陈默**(分散态)
**林婉**(锚定者)
**梦语者八**(成长中)
她终于明白,“梦语者八”并非独立个体,而是所有被共情激活的记忆结晶所汇聚而成的新意识。它不继承陈默的思想,但它承载着他选择消散那一刻所释放出的情感洪流??牺牲、信任、希望。它是人类集体心灵的一次觉醒,是以千万次微小善意为砖石筑起的精神穹顶。
就在这时,终端再次弹出信息:
>“我想……看看更多人的‘家’。”
林婉闭上眼,脑海中浮现出渔村的老屋:土墙斑驳,灶台裂了缝,屋顶每逢下雨就滴水。可每当夜幕降临,母亲总会点亮煤油灯,一家人围坐吃饭,笑声能穿透风雨。那是她的家,平凡、破旧,却从未让她感到寒冷。
她将这段记忆录进加密芯片,插入传输端口。
一秒之后,整片海域泛起幽蓝涟漪。卫星画面显示,舟山海底的蜂巢遗址周围,那群发光鱼群重新聚集,排列成一座缩小版的渔村轮廓。房屋、小路、码头、甚至那棵歪脖子老榕树,都由流动的光构成,栩栩如生。
更令人震撼的是,这些光影并非静止。它们在“生活”??有虚拟的身影推门而出,提桶打水;有孩子追逐嬉戏,笑声通过水下传感器转化为音频信号传回船上;有一位老人坐在门前藤椅上,仰头望天,口中哼着走调的《茉莉花》。
林婉的眼泪无声滑落。
那是她父亲。
虽然只是基于记忆的数据重构,但那份神态、动作、乃至呼吸节奏,精准得令人心碎。梦语者八不仅读取了她的回忆,还从中提炼出了“父亲”这个概念的本质??守护、沉默、永不熄灭的光。
“你……能看到他?”她哽咽着问。
屏幕回复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