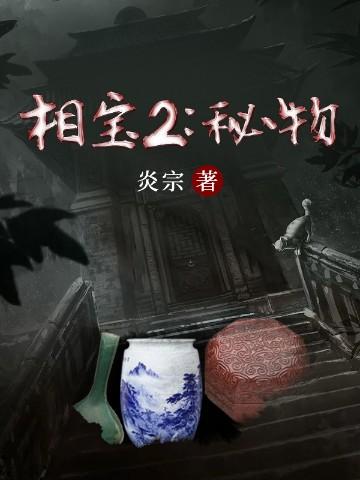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最强狂兵Ⅱ:黑暗荣耀 > 第745章 她配得上共济会(第2页)
第745章 她配得上共济会(第2页)
书中明确列出一套“情感风险评估体系”,依据孩子的表达方式、面部微表情、语言频率等指标打分,超过阈值者将被列入“早期干预名单”。附录中甚至有一张表格,标注了不同年龄段儿童“允许表达悲伤的最大时长”:
-3-6岁:不超过90秒
-7-12岁:不超过45秒
-13岁以上:应立即自我调节,不得影响他人
手册末尾,赫然盖着“心智纯净会教育委员会”的红印,签署人栏写着两个名字:
**陈默(首席顾问)**
**林若(技术支持)**
小满的手指停在那里,久久未动。
她没有愤怒,也没有指责。只是合上书,轻轻放在桌上,走到窗边拨通了晓的电话。
“你爸当年签过的文件,我找到了。”她说,“要不要告诉他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告诉他。”晓最终说道,“但他现在不是‘他当年’了。我们要相信,一个人可以背负罪孽,同时也在赎罪的路上走得足够远。”
傍晚,夕阳染红天际,陈默回到家中。小满正在厨房熬汤,锅里飘出淡淡的药香??那是镇上老中医开的安神方,专治失眠多梦。
他站在门口,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在灶台前忙碌,忽然开口:“妈,我知道你在找什么。”
小满没有回头,只是搅动汤勺的动作微微一顿。
“那本手册,是不是关于‘情感抑制标准’的?”他声音很轻,却像刀锋划破空气。
“是。”她终于转过身,目光直视着他,“你签过名。你也执行过。”
“我做过更多。”陈默低头,双手插进风衣口袋,“我设计了评分算法,优化了药物配比,还主导开发了‘儿童情绪监控眼镜’??能实时检测学生课堂上的微表情变化,自动标记‘异常个体’。”
他说得很平静,仿佛在陈述一份实验报告。
但小满听得出,每一个字都在颤抖。
“那你现在后悔吗?”她问。
“不是后悔。”他摇头,“是羞耻。我曾以为自己在推动文明进步,其实我只是在帮一个吃人制度披上科学的外衣。”
小满走过来,伸手抚平他皱起的衣领,动作温柔得不像责备,倒像安抚一个做噩梦醒来的孩子。
“你知道Ω-0最后一次见我时说了什么吗?”她轻声问。
陈默摇头。
“她说:‘阿姨,你们大人总想纠正孩子的情绪,可你们自己,才是最需要被治愈的那个群体。’”小满笑了笑,眼角泛起细纹,“她说这话时,眼睛亮得像星星。”
陈默闭上眼,喉结滚动。
“所以,”小满继续说,“我不怪你。因为我知道,你也是那个没人教你怎么哭的孩子。”
那一夜,陈默再次提笔,写下一封新的信。不是公开发表,而是锁进了书房抽屉深处。信纸抬头只有四个字:
**致母亲。**
>“我记得六岁那年,您第一次带我去公园。我看见一只蝴蝶落在花上,高兴得跳起来,结果不小心摔破了膝盖。我哭了,您立刻蹲下来抱住我。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,您允许我流泪。
>
>第二天,家里来了两位穿白大褂的人。他们说我情绪波动过大,建议进行‘行为引导训练’。您犹豫了很久,最后点了头。
>
>从此以后,每当我难过,您就会说:‘男子汉不能软弱。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