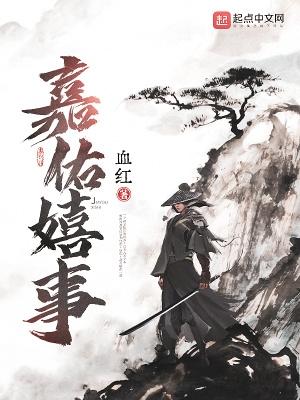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直播鉴宝:你这精灵可不兴育啊! > 第534章 永动机式特训战斗爽雷鸣深处不得了的存在(第2页)
第534章 永动机式特训战斗爽雷鸣深处不得了的存在(第2页)
女孩紧紧攥着纸片,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
第二天清晨,暴雨停歇,山间雾气缭绕。阿禾和周雯收拾行装准备离开。村民们悄悄送来干粮和草药,没人多问她们要去哪里,但每个人的眼神都在说同一句话:我们会守住这里的光。
临行前,村长递来一只竹筒,里面卷着一卷手工抄写的纸页。“这是我们村里几位老人昨夜熬夜整理的。”他说,“过去不敢说的事,现在都想起来了。有三个老人讲述了当年亲眼所见的批斗大会,有两个妇女回忆了亲人失踪的经过……我们都录了音,转成文字,交给你。”
阿禾双手接过,郑重地放入背包最内层。她知道,这不仅仅是一份资料,而是一座村庄集体记忆的觉醒。
两人徒步穿越密林,前往下一个联络点??一座隐藏在澜沧江支流峡谷中的废弃气象站。那里有一台老式电报机,仍能通过短波连接国际共感网络。途中,周雯突然停下脚步,盯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:“不对劲……最近三天,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量伪造的‘声渊’广播信号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阿禾皱眉。
“有人在模仿我们的传输协议,发布虚假音频。”周雯脸色凝重,“比如一段所谓的‘王秀兰遗书’,内容却是忏悔自己‘误入歧途’,劝后人不要追随‘极端思想’。还有人冒充李文清的学生,录制演讲,声称他已经‘精神康复’,并呼吁停止传播‘未经核实的历史谣言’。”
阿禾冷笑:“他们在制造混乱,让人分不清真假。一旦公众开始怀疑所有声音的真实性,真正的记忆就会被淹没在信息泥潭里。”
“更可怕的是,”周雯低声补充,“这些假音频的情绪波动曲线,竟然与真实录音高度吻合。说明对方掌握了共感共鸣的核心算法??要么是内部叛徒泄露技术,要么……就是‘净化工程’早就研究过我们的一切。”
阿禾沉默良久,最终开口:“那就让我们发出更真、更痛、更具穿透力的声音。真实永远比谎言更有力量,前提是它足够勇敢地暴露伤口。”
抵达气象站时已是深夜。这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早已荒废,墙体斑驳,屋顶塌陷半边。但在地下室,那台德国产的老式莫尔斯电报机依然完好,铜线未锈,按键灵敏。周雯迅速架设天线,将最新整理的音频数据转化为脉冲信号,准备以最原始的方式向世界发送。
就在她即将按下发射键的瞬间,警报骤然响起??来自远程监控系统的紧急提示:**“清源行动”特别小组已锁定云南南部区域,正调派无人机集群进行热成像扫描,目标特征匹配度98。7%。**
“他们找来了。”周雯咬牙,“最多两小时就会到。”
阿禾却异常平静。她取出录音机,贴在电报机外壳上,开启同步录制模式。“那就让这台机器成为最后一个见证者。”她说,“不管我们能不能逃出去,这段操作过程本身,就是一段历史。”
她开始口述:
>“这里是阿禾,时间是2025年4月7日凌晨3点12分。我们在云南边境某处秘密站点,正在进行第十五次大规模音频释放。内容包括陈志远日记全本、王秀兰后续审讯录像残片、以及超过两千名匿名幸存者的口述实录。我们知道敌人正在伪造我们的声音,试图瓦解信任。但我们坚信,真正的共感能力不在技术,而在人心。只要你愿意倾听,就能分辨出哪一个是颤抖着说出真相的声音,哪一个是冰冷计算出来的谎言。”
她顿了顿,目光扫过昏暗的地下室,仿佛透过时空望见无数双聆听的眼睛。
>“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:今天我们所做的,并非为了复仇,也不是为了推翻什么。我们只是想让那些被抹去的人,重新拥有一次‘被记住’的权利。他们的名字不必登上纪念碑,不必写进教科书,只需要在一个孩子的梦里出现一次,就够了。只要有人梦见他们,他们就没有真正死去。”
周雯完成了最后调试,回头看向她:“准备好了吗?”
阿禾点点头:“发吧。用最大功率,持续十分钟。之后立刻销毁设备,切断所有痕迹。”
电流嗡鸣,电报机的按键自动跳动起来,哒哒声如心跳般规律而坚定。无形的声波穿过潮湿空气,顺着天线射向高空,混入大气层中的电磁乱流,随风飘向未知的远方。
十分钟后,信号终止。周雯砸毁电报机,焚烧线路图。阿禾则将录音机藏进墙缝,用碎砖封死。“也许一百年后,有人会挖到这里。”她说,“那时候,希望他们还能听懂这段话。”
两人趁夜撤离。黎明前,一架黑色无人机掠过山谷,红外探测显示此处无人活动,遂标记为“误报”,返航。
然而就在同一时刻,远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位音乐学院学生,在调试古董收音机时意外捕捉到一段奇异信号。她将其录下,上传至个人博客,标题为《昨夜收到的神秘电码,听起来像有人在哭》。短短六小时内,该音频被下载十万次,世界各地陆续有人反馈:在同一频段收到了相同内容。
语言学家破译了部分莫尔斯代码,发现其中嵌套着多重加密信息。最令人震惊的是,当把音频倒放并加速1。5倍后,竟浮现出一段清晰的人声吟唱??正是那首老民谣:
>“长夜漫漫不见星,
>谁在墙角写姓名?
>笔尖划破纸背疼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