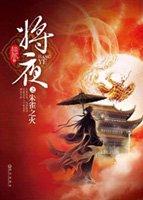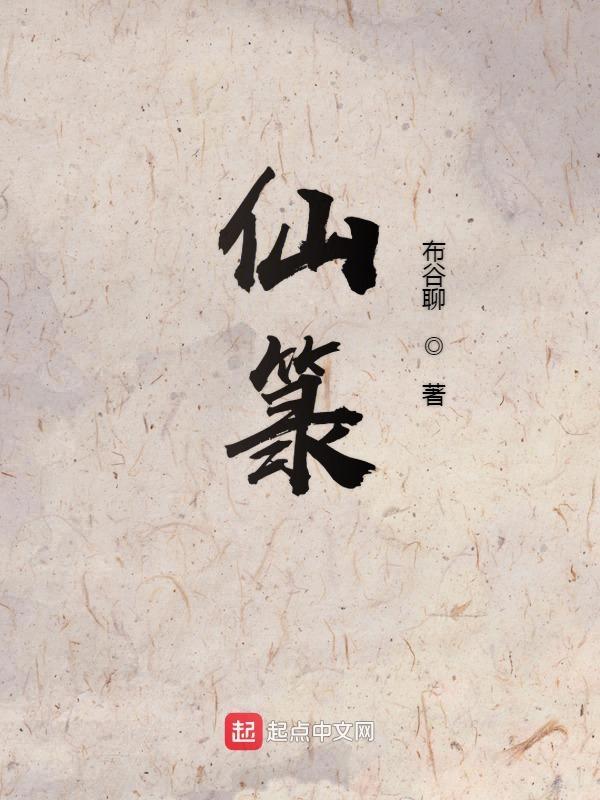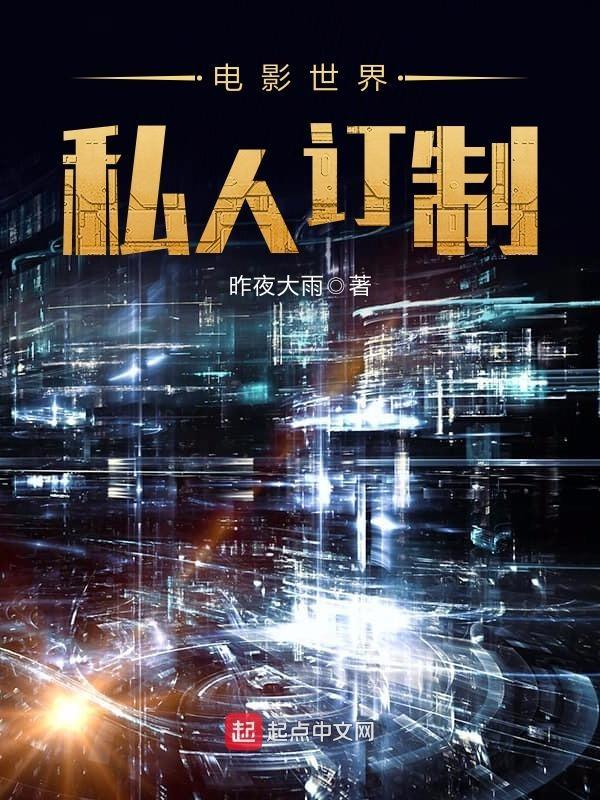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华娱情报王 > 381 与贾老板的默契新三国开播猛吕布出场(第1页)
381 与贾老板的默契新三国开播猛吕布出场(第1页)
李晓路跟着霍丝燕到了地方才发现,她俩误会了。
颜礼叫霍过来的目的与她俩想的不一样,而是让她来应酬。
而之所以颜礼让霍丝燕过来,原因是今天和颜礼应酬的正是乐视贾老板。
说白了,颜礼是给。。。
黄枝站在阳台上,手指还停留在手机屏幕上,那句动态已经悄然发布。阳光斜照在楼下的石板路上,映出斑驳的影子,像是一张无形的信息网,正缓缓铺展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他忽然觉得,这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,而是一个由千万个微小选择构成的认知共同体??有人转发,有人质疑,有人查证,有人传播真相。
手机再次震动,是于征发来的消息:“镜渊平台昨晚拦截了七百三十六份伪造报告,其中四百一十二份来自境外IP,集中在东南亚和东欧。”后面附了一个加密链接,“我们抓到了一个自动化生成伪清源文档的AI集群,模型训练数据里混入了大量真实‘清源’接口响应样本。”
黄枝眉头一紧。这意味着,敌对势力不仅在模仿系统外观,还在逆向学习它的行为逻辑。更可怕的是,他们能获取到真实的交互数据??要么存在内部泄露,要么有人通过合法调用不断采集反馈,构建训练集。
他立刻拨通于征电话:“启动‘蜂巢审计’,从三个月内的所有公开API请求中筛查异常模式。重点排查高频、低内容差异、跨区域轮换IP的行为特征。”
“已经在做了。”于征声音低沉,“但有个问题??部分疑似攻击流量,是从教育系统的备案账号发出的。比如甘肃某中学、湖南一所职校,甚至还有国家图书馆的开放终端。”
黄枝沉默片刻。这不是单纯的黑客行为,而是利用公共资源进行隐蔽渗透。这些人懂得规避商业云服务的风险审查,又披着“学术研究”或“公众查证”的外衣,极具迷惑性。
“把数据脱敏后提交网信办技术局,同时抄送教育部信息中心。”他说,“不能只靠技术防御,得让制度也醒过来。”
挂断电话,他转身回屋,却发现董萱正坐在沙发上翻看一本旧相册。那是陈婉生前与黄枝合拍的一部电影宣传册,封底印着一句台词:“你以为你看清了世界,其实只是它想让你看见的样子。”
“最近总梦见她。”董萱轻声说,“梦里她在后台化妆,一边涂口红一边问我:‘现在大家相信你了吗?’我说还没完,她说那就继续讲下去,别停。”
黄枝走过去坐下,握住她的手。他知道,董萱作为陈婉最亲密的朋友之一,从未真正走出那场舆论风暴。而如今,“清源”的每一次成功辟谣,都像是对逝者的一种迟来告慰。
“下周我要去日内瓦。”他说,“联合国峰会之后,有几个国际组织想谈合作。欧盟数字事务署提出共建跨境验证联盟,希望将‘镜渊’标准纳入他们的事实核查互认机制。”
董萱抬头看他:“那你得小心。国外有些机构嘴上说支持透明,背地里却想掌握主导权。一旦标准被改写,你的开源也就失去了意义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黄枝点头,“所以我准备带一份‘反制协议’过去??任何采用‘镜渊’框架的国家或平台,必须承诺三项原则:不用于政治打压、不限制公民查证权利、不得擅自修改核心验证逻辑。否则自动终止技术授权。”
董萱笑了:“你还真是把代码当宪法用了。”
“因为这就是新时代的基本法。”黄枝认真道,“当谎言可以用AI批量生产,真相就必须有不可侵犯的边界。”
两天后,黄枝启程飞往瑞士。临行前,他在机场接到林晓电话:“贵州苗寨那位阿婆,昨天带着六个老人组团注册了‘民间辟谣志愿者’,她们建了个微信群,叫‘银发打假队’。昨晚成功识别一起冒充村干部通知‘集体领补贴需先交手续费’的诈骗信息,阻止了十七人转账。”
“把她们的故事做成短视频吧。”黄枝说,“不用配音,就用原声,让全国听听这些老人是怎么说话的。”
飞机穿越云层,舷窗外一片雪白。黄枝闭目养神,脑海中却不断浮现陈婉视频里的画面。他知道,自己正在完成一场跨越生死的约定??不是为复仇,而是重建信任。
抵达日内瓦已是当地时间傍晚。接机的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科技参赞,姓李。车上,对方递给他一份简报:“明天发言前,美、英、法三方代表会联合提出一项修正案,试图将全球事实核查体系纳入‘多边共治’框架,实质是由西方主导的标准委员会来认证各平台资质。”
黄枝冷笑:“又是老套路??谁掌握标准,谁就定义真相。”
“更麻烦的是,他们引用了你在微博说过的话:‘真正的安全在于透明’,反过来说你既然主张公开,就应该接受国际监管。”
黄枝眯起眼:“那我正好告诉他们,透明不等于任人宰割。我可以开放算法,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以‘治理’之名行‘垄断’之实。”
次日上午,全球数字治理峰会主会场座无虚席。各国政府代表、科技企业领袖、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齐聚一堂。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各国普通人使用事实核查工具的画面:印度妇女比对着疫苗谣言,巴西青年揭穿政客虚假承诺,北欧学生用APP验证社交媒体广告……
轮到黄枝登台时,全场安静下来。
他没有拿稿子,只带着一台平板走上讲台。灯光下,他的声音平稳而坚定:
“两个月前,在中国西南的一个苗寨,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第一次学会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查验信息真伪。她告诉我:‘以前我们怕骗子上门,现在我知道,骗子最怕我们开机。’”
台下有人轻笑,随即转为掌声。
“我想说的是,技术从来不是精英的专利。真正的数字正义,不在于谁能建造最强大的服务器,而在于谁能教会最多普通人按下那个‘查证’按钮。”
他调出一张图表:“这是‘清源’上线以来的数据曲线。每天超过五百万次查证请求,八成以上来自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。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曾经最容易被谣言伤害的人群,现在成了最积极的真相守护者。”
稍作停顿,他直视前方摄像机:“有人问我,为什么坚持开源?因为我相信,真相不该被锁在某个公司的数据库里,也不该由某个国家的政府独家解释。它应该像空气一样自由流动,但必须有清晰的来源标记,就像水有河床,风有方向。”
此时,英国代表举手要求提问。他语气克制但锋利:“您强调透明与共享,但我们注意到,贵方拒绝加入现有的国际事实核查联盟,并单方面设立技术准入门槛。这是否构成新的数字壁垒?”
黄枝微微一笑:“请问,你们联盟目前认证的十四个成员中,有几个来自非洲?几个来自拉美?有没有任何一个代表亚洲乡村社区的声音?”
对方语塞。
“我不是反对合作,而是反对伪合作。”黄枝继续道,“如果所谓‘共治’只是少数发达国家轮流坐庄,那不过是旧霸权换了个名字。我们可以共建规则,但前提是平等参与。我提议成立一个‘全球基层信息权益观察团’,由每个大洲推选三位来自偏远地区的普通用户代表,直接参与标准审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