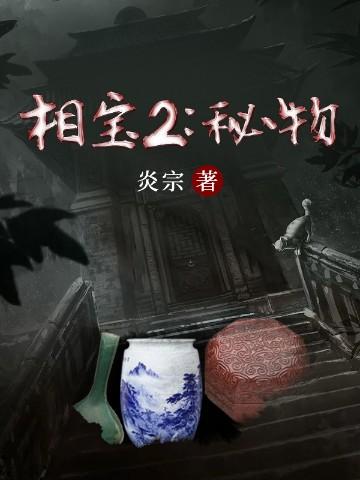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我真没想下围棋啊! > 第四百九十三章 天下劫(第1页)
第四百九十三章 天下劫(第1页)
“立下?”
朝韩棋院内,众人皱眉,思索片刻,脸上仍是露出不解之色:“这一手立下要将边线这里补实,不给黑棋未来打入的机会,说起来并不差,但是,于事无补啊?”
就连车允赫,也是摸着下巴,紧缩眉。。。
车子在广西与云南交界处的一条窄道上抛锚了。夜色浓得像墨,四周山影如兽伏卧,风从谷底爬上来,带着湿冷的草腥味。我们下车查看,沈砚之蹲在轮胎旁用手电照着漏气的侧壁,眉头没皱一下:“补不了,得换。”
我翻出备用胎,却发现螺丝锈死,扳手拧不动。两人折腾近一小时,手心磨破,汗水混着泥灰流进眼睛。远处忽然传来犬吠,接着是脚步声??两个穿胶鞋的少年提着马灯走来,一个背工具包,一个牵着头矮脚黄牛。
“你们是来说话棋的吧?”年长的那个问,声音清亮,“村里的娃都等着呢。”
原来这叫“龙脊坳”的地方虽地图上找不到,却早已通过口信得知我们的行程。他们用牛车把我们和设备拖回村里,在一间废弃的粮仓里安顿下来。粮仓四面通风,屋顶漏月光,但被村民们连夜铺上了木板、垫子和旧棉被。
第二天清晨,孩子们陆陆续续来了。最小的不过六岁,最大的已初中毕业却因家贫辍学。他们不吵不闹,安静地坐在门槛上等。有个女孩一直低头抠手指,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她叫阿?,老师悄悄说:“她三年没开口说过一句话,连‘嗯’都不肯。”
我们照例准备画棋盘,可地面坑洼不平,石灰粉刚撒上去就被风吹散。正发愁时,几个妇女抬来一块巨大的青石板,说是祖上传下的磨刀石,几十年没人用过了。“就在这上面下。”她们说,“石头硬,话也沉得住。”
我们在石板上用红漆勾出十九路格线,虽歪斜却不失庄严。第一枚子由一位老猎人落下。他年轻时追野猪摔断腿,从此再不能进山,性情也变得孤僻暴戾。他拄拐上前,从怀里掏出一颗干瘪的松果,放在左下角:“**我对不起那头母鹿。它带着崽,我没放过它。**”
全场静默。一只麻雀飞落在石板边缘,啄了啄松果,又扑棱飞走。
接着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,父亲酗酒殴母,他曾在一次争吵中抄起菜刀吓退父亲,事后却被全村指责“不孝”。他站在棋盘前,双手攥紧裤缝,声音颤抖:“**我不是想砍他……我只是想让她别哭了。**”
话音落,眼泪砸在地上,溅起一小团尘土。
轮到阿?时,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她站在原地不动,姐姐轻轻推她后背。她终于迈步,走得极慢,像踩在冰面上。到了棋盘中央,她蹲下身,从口袋里摸出半截蜡笔??那是去年支教老师留下的礼物,她一直舍不得用。她没有落子,而是趴下去,在天元位置画了一朵花:五片花瓣,中间一个小圆点。
没有人催她说话。良久,她抬起头,望着我们,嘴唇微动,终于挤出三个字:“**我想……唱歌。**”
那一刻,整个粮仓仿佛被阳光穿透。几位年长妇女抹起了眼角,一个老太太颤巍巍站起来,从怀里掏出一支竹笛:“阿?爱听我吹《月光调》,小时候总跟着哼,后来她妈病逝那天,她就再也不出声了。”
笛声响起,清越悠远。阿?闭上眼,轻轻张嘴,发出一个单音。那声音干涩、断裂,像是久未开启的门轴,可它确确实实存在。一个音接一个音,她竟完整唱完了整首曲子。歌声落下,满屋啜泣。
我们录下了这段音频,存入录音笔最深处。沈砚之低声对我说:“这才是真正的‘落子无悔’。”
当晚,村里为我们办了简陋的接风宴。没有酒肉,只有红薯粥和腌蕨菜,但每户人家都送来一点心意:一把花生、两只鸡蛋、一束野葱。席间,村主任说起一件往事:二十年前,县里曾派过一批心理辅导专家来做过“留守儿童关爱项目”,住了三天,拍了些照片就走了。后来问卷显示,“满意度百分之百”,可孩子们什么也没得到。
“你们不一样。”他说,“你们不是来‘帮’我们,是来‘听’我们。”
我心头一震。想起城市里那些高大上的公益论坛,PPT做得精美绝伦,数据图表琳琅满目,可谁真正蹲下来,看过一个孩子眼里的光?
第二天,我们开始培训本地志愿者。选出的六人中有教师、退伍军人、返乡青年,还有那位吹笛的老太太。我们教他们使用录音设备、整理语料、建立简易档案,并设计了一套“语音漂流瓶”机制:每个孩子录一段心里话,随机传送给另一个村落的孩子收听,对方听完后需回应一句“我听见了”,再录下自己的话继续传递。
“这不是游戏。”沈砚之强调,“这是信任的链条。一旦开始,就不能中断。”
临行前夜,暴雨突至。雨水顺着粮仓缝隙灌进来,我们急忙用塑料布盖住设备。忽然,门外传来喧哗声。十几名村民冒雨赶来,手里拿着油毡、竹席、破伞,二话不说就开始加固屋顶。有个七八岁的男孩抱着一卷电线跑来:“我爸说,喇叭还能响!”
他们把村广播站的扩音器搬来,接上我们的笔记本电脑。沈砚之打开文件夹,播放这些日子收集的声音??木扒的低语、娜玛的愿望、盲童的提问、阿?的第一句歌唱……一条条话语在雨夜里回荡,穿过泥泞的院落,飘向漆黑的山峦。
一位老妇人站在雨中听完孙女说“奶奶做的糍粑最好吃”,突然嚎啕大哭。她儿子早年外出打工死于矿难,儿媳改嫁,她独自拉扯两个孙子,从未听过一句温情的话。此刻,她跪在湿地上,朝着声音的方向磕了个头。
雨停时已是凌晨。我们疲惫不堪,却无人入睡。沈砚之坐在门槛上写日记,我靠在他肩上看星星。忽然,手机震动??是伊力亚尔发来的视频消息。
画面中,新疆的孩子们正在沙漠边缘搭建一座“声音塔”:用废旧铁皮桶、玻璃瓶、风铃串成一根高柱,顶端绑着一块写着“听懂的心”的木牌。风吹过时,瓶子碰撞作响,仿佛无数人在低语。
“我们把它叫做‘会走路的耳朵’。”伊力亚尔笑着说,“只要风不停,声音就不会消失。”
我鼻子一酸。回复道:“告诉孩子们,怒江的风已经带回了娜玛的话。”
第三天清晨启程。村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,直到山路拐弯再也看不见。车行至半途,我发现副驾上的雪莲种子不见了。回头翻找,见沈砚之正从背包夹层取出一个小布袋,里面装着几粒白色种籽,还有一张纸条:“留给下一个不开口的孩子。”
我笑了:“你什么时候换的?”
“昨晚。”他说,“有些东西,不能带走,只能留下。”
接下来的两周,我们穿越滇桂黔三省交界地带,足迹延伸至贵州册亨、云南广南、广西那坡。每一站都出乎意料地有人等候。有的村小学自发组织“每日一言”活动,每天晨读前必须有一个人说出一句真心话;有的寨子将棋盘刻在祠堂门前的石阶上,新人结婚、孩子满月都要去走一步;甚至有一位乡村医生,开始在问诊时加一句:“除了身体,心里有没有哪里疼?”
在贵州望谟的一个布依族村寨,我们遇到了最特殊的情况。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山体滑坡,三十多个孩子遇难,幸存者长期陷入集体沉默。村委会试图重建心理防线多年未果。
当我们提出重开“无界棋局”时,村长犹豫良久才点头:“可以试,但请允许我们加个规矩??每个人落子前,要先念一个名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