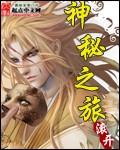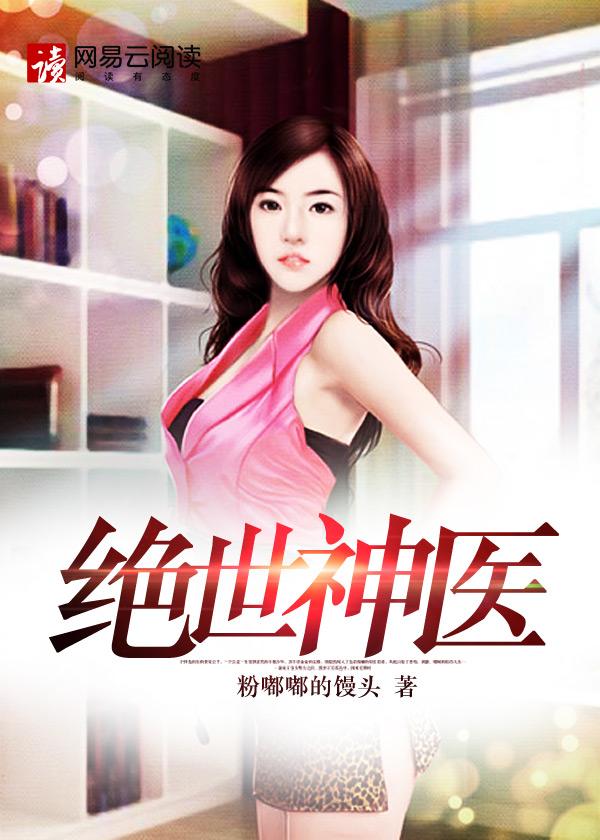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天工宰执之熙朝风云 > 第120章 金角湾火链(第3页)
第120章 金角湾火链(第3页)
至和三年正月望日,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首次亲临火器作,却未穿紫袍,而换一袭素白长衫,腰系“宋式玉凉带”,带扣为“双头鹰”衔十字,显是特意为“学生”身份换装。
讲堂中央,摆一座“玻璃沙盘”——以铅玻璃为底,沙面覆白绢,再以石墨棍画“地中海”轮廓,水纹以蓝粉撒成;岸边插各色小旗:红为宋,金为威尼斯,白为热那亚,紫为拜占庭,绿为撒拉森。
皇帝面前,摊一张“比例尺”新图,图上以“汴京里”为单位,一寸代表十里。
授课者,却不是章衡,而是年仅二十的汴京“军器监少年匠作”刘惟清——此次西来,专责“火器上船”之算学与实务。
少年以汉语开讲,通译实时译为希腊语:
“炮击之要,一在测距,二在量药,三在后坐。
测距用‘量角仪’,以三角算斜边;量药用‘石墨尺’,以比例算爆速;后坐用‘鲸油弹簧’,以伸缩算力矩。
三者皆准,则百发百中;一毫不准,则失之千里。”
皇帝听得入神,忽举手提问,竟用生涩汉语:“若敌舰横移,角速如何算?”
刘惟清一愣,旋即取“movableruler”——一条可滑动的铜尺,尺上刻“瞬时角速”刻度,一端固定,一端随敌舰移动,尺背齿轮带动指针,即刻读出“度息”。
皇帝亲手试之,连读三次,皆准,不禁大喜,转头对章衡道:
“宰相所言‘五年成匠’,朕今信矣!”
章衡笑答:“陛下若肯学,三年可成‘算学炮匠’;陛下若肯教,罗马少年皆可为匠。如此,火链不再靠宋人,而靠罗马自己。”
皇帝沉思片刻,忽命人取来一只“紫绒锦盒”,盒内是一卷“拜占庭皇家星表”——上起托勒密,下迄本朝,含恒星一千零二十二颗,皆以希腊字母编号,旁注“黄道坐标”。
“朕以此表,换宋人‘活字印刷’与‘玻璃镜筒’之技,另加一条件——”
他目光灼灼:“朕要在圣索菲亚穹顶,加一幅‘宋—罗马合璧星图’,让双头鹰与日月龙,同悬于上帝之眼!”
章衡拱手:“愿为陛下,亦愿为星空。”
三日后,圣索菲亚大教堂。
穹顶高五十五丈,首径三十三丈,原为拜占庭“基督万能”马赛克,却因数次地震,部分星位剥落。
宋人匠作搭起“悬空竹棚”——以汴京“井字架”为基,再以滑轮、绞盘升降,棚上铺轻质铅玻璃板,透光不反光,工匠于板上作业,可白日不举火。
少年匠作刘惟清单手挽“安全绳”,一手以“金钢钻”在穹顶旧马赛克间钻孔,再以“铜铆钉”固定新的“玻璃星图”——每一块玻璃,皆以铅玻璃为底,内嵌金丝,构成“二十八宿”与“希腊西十八星座”同图:
角宿一,对应“室女”Spica;斗宿,对应“南冕”aAustralis;银河,则以淡金玻璃流成一条光带,自东北而西南,横贯穹顶,象征“丝绸之路”连接东西。
最中心,一块首径三尺的“日月同辉”圆玻璃,以双层玻璃夹“金箔”,日如金轮,月似银钩,同悬于基督“万能”像上方,既不相掩,亦不相争。
当最后一块玻璃嵌好,夕阳恰好透窗,射在穹顶——
霎时,整个教堂内部,仿佛被一双巨手撒下万点金星:
角宿呈幽蓝,斗宿呈淡紫,银河是流动的金,日月则是一轮炽烈、一弯清冷,同时落在信徒与工匠的肩头。
皇帝亲自击响铜钟,钟声里,拉丁神父与希腊修士同诵《荣耀颂》,宋人乐工则以“筚篥”“琵琶”和之,音律一高一低,一缓一急,却在穹顶回声里奇妙交融,如两条河流并入同一海口。
音浪与光浪交织,信徒们不由自主抬头,只见“宋星”与“希腊星”同辉,一时竟分不清,哪是旧天,哪是新天。
星图既成,实战随之。
皇帝要在全城百姓面前,演示“宋—罗马合璧火器”,以证“新火可守旧都”。
地点,选在金角湾最窄处——湾宽仅七百步,两岸以“铁索浮桥”相连,桥可升可降;北岸设“靶墙”,以十层旧船板叠成,厚三尺,模拟“敌舰舷侧”;南岸,便是“宋—罗马火器作”前沿试炮场。
巳时正,皇帝与皇后同登“紫袍台”,百姓万人空巷,拥于湾岸,瓦良格卫队以斧柄隔出通道。
章衡亲操第一门“合璧炮”——炮身外以拜占庭“紫铜”铸成浮雕双头鹰,炮尾却用宋人“开合式炮闩”,炮管内壁以“水力钻床”刻出“双锥膛线”,炮弹为“子母锥形弹”,母弹破板,子弹破人。
靶墙设于七百步外,以“风帆”为帆,帆后系“浮木”,帆面画“绿底弯刀”——象征撒拉森海盗。
皇帝手执“紫绒令旗”,亲自下令:
“放!”
轰——
炮口喷出三尺紫焰,弹丸划出一道低平弧线,竟在距靶十步处提前裂爆,二十枚锥形子弹如天女散花,“噗噗噗”同时命中帆面,七层帆布瞬间被撕裂成蝶,帆后浮木被击得木屑横飞,一块尺长碎片被气浪掀起,高高抛上半空,又“啪”一声落入湾面,溅起丈高水柱!
百姓先是寂静,继而爆发雷鸣般欢呼: